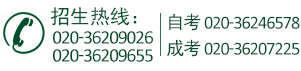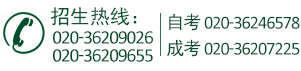学习任何一门语言(尤其是除母语外的第二语言),听说读写的训练必不可少,但在二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却扮演着比“说”和“写”更重要的角色,借用计算机术语可归纳为GIGO理论,即Garbage in, garbage out.(低质量的输入导致低质量的输出)。在语言里,所谓“输入”(input), 当然指的就是“听”与“读”,而“输出”当然指“说”与“写”,有些二语学习者学了十几、几十年外语,仍然无法说出地道的外语,当然就是因为低质量的输入导致低质量的输出。而如何提高输入质量,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属背诵。从记忆规律的角度来说,所背诵的总是不可避免的要遗忘的。人的记忆遗忘的速度是和重复的次数成反比的。要想永久的记忆,那么就必须反复地背诵.大脑越用越灵活,在反复的诵读背诵中增强了大脑的记忆力,积累也就多了,在运用的时候就可以得心应手了。对于母语学习如此,对外语(二语习得)更是如此。
美国语言家Krashen(1982)提出了著名的第二语言习得五个假设。其中输入假设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即语言习得是通过语言输入来完成的,教学的主要精力应放在为学生提供最佳的语言输入上,最佳的语言输入必须具备以下特点:①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②既有趣又有关(interesting and relevant);③非语法程序安排(not grammatical sequenced);④要有足够的输入量。其中可理解性输入是语言习得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语言习得的至关重要的条件。Krashen认为,背诵是主要的语言输入方式之一。上述几点,实际上提出了对背诵内容的基本要求。
古今中外,那些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大师很多都把背诵视为习得一门外语的不二法门。下面仅举辜鸿铭为例: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他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踏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诵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 了。
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时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笔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22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学生可比。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他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
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
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从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腊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方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从学习语言过程看:我们的教学条件及环境决定了学生不可能像学习母语那样学习英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材料来学习英语。人们学母语无一不是从口语入手,逐步发展为书面语。但我们的外语教学必须遵循语言学习的共同规律——在听说的基础上发展读写。听说与读写相辅相成,口语与书面语同步协调发展,才能培养学生的语感,训练用外语思维,正确而熟练地运用所学材料,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学习水平,培养学生的语感。
实践证明,在英语篇章背诵的教与学的过程中,学生掌握背诵英语课文的方法越多,学生就会拥有更丰富更灵活更有选择性的地道表达方式;从而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也能更好的培养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以及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因此,在有着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教学理论的当下,英语篇章背诵的教学还是值得大力提倡。